前言 #
Matei Candea 主编的 Schools and Styl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去年在国内出版了,由中国农业大学的王晴锋老师翻译,中文名为《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人类学理论的流派与风格》。这本教材在国内的风评很好,一反往常教材将理论「划分为一块块(流派、理论或『范式』,也就是各种『主义』)」的古典写法 [1]
[1] 关于范式这部分的说明,将另外作为单独的阅读札记部分记录。
当然,这本教材还以其涉及行动者网络理论、本体论转向等前沿内容而闻名,这些理论在市面上的教材中都不多见。就我而言,甚至就许多人类学或民族学科班出身的学生,乃至教职人员而言,都不一定知晓何为近年来提得比较多的「本体论转向」。
就目前的阅读体验来看,由于过去翻阅过夏建中、宋蜀华等学者编著的传统教材,我对较为传统经典的理论有一定的熟悉度,因此在这本《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中对进化论、扩散主义(或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感到启发较多,感受到了理论的「对话」——这或许也是这本教材试图给读者带来的体验,我将此理解为对人类学的想象应当挣脱过去的范式思维,学会寻找理论的脉络,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对话交流,认识到即便是旧的理论也可以在新的时代里激发活力。 [2]
[2] 3月24日,我前往硇洲见了方静师姐,和她聊了许多,基于她和我的对话,以及我过去的学习经验,我将自己(仅个人)对人类学的想象和理解的一个面向概括为「故事」,但尚且没来得及进行写作。此次阅读这本教材,则是试图再将一个面向概括为「对话」。
截至今日,我完成了五个篇章的阅读(不过,相较传统的教材,其中的「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看得云里雾里)。由于每个篇章都由不同的作者进行写作(这并不影响篇章中体现的理论对话与回响),我预备基于不同的篇章形成不同的札记。
这一篇从 Fredrik Barth 和他的交易主义开始。当然,关于进化论、扩散主义(或传播论)、(结构)功能主义部分也是相当精彩的, Candea 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介绍,待后续我再慢慢整理。
为什么是 Barth 和交易主义 #
并不是因为偏爱 Barth [3]
[3] 国内对 Fredrik Barth 的翻译并不统一,有称作「弗雷德里克·巴特」,也有「费雷德里克·巴斯」,据此,我认为写作时不如保留原英文名,只做一次注释即可。不过,保留英文原名的习惯我多在春花的写作中见,我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可以说,其实正因为 David Sneath 对 Barth 的介绍比较清晰具体,让我终于知晓「谁人是 Barth?」,「交易主义又究竟在讲什么?」——或许是习惯于过去教材对理论的介绍,翻开《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时,出现的「交易主义」实在显得太突兀,而且 Sneath 还将交易主义与 Evans-Pritchard 在努尔人社会中提出的「裂变原则」 [4]
[4] 如我过去所言,我对人类学比较系统的想象从阅读《努尔人》开始,虽然当时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看懂。
也是从终于记住 Barth 是谁开始,我才顺道串联起了过去的模糊记忆:诶!经典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也是 Barth 写的!你以为 Barth 只是研究政治人类学吗?不是,作为族群研究典范性著作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也是 Barth 写作的!以及,黄应贵先生也在《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介绍政治人类学时提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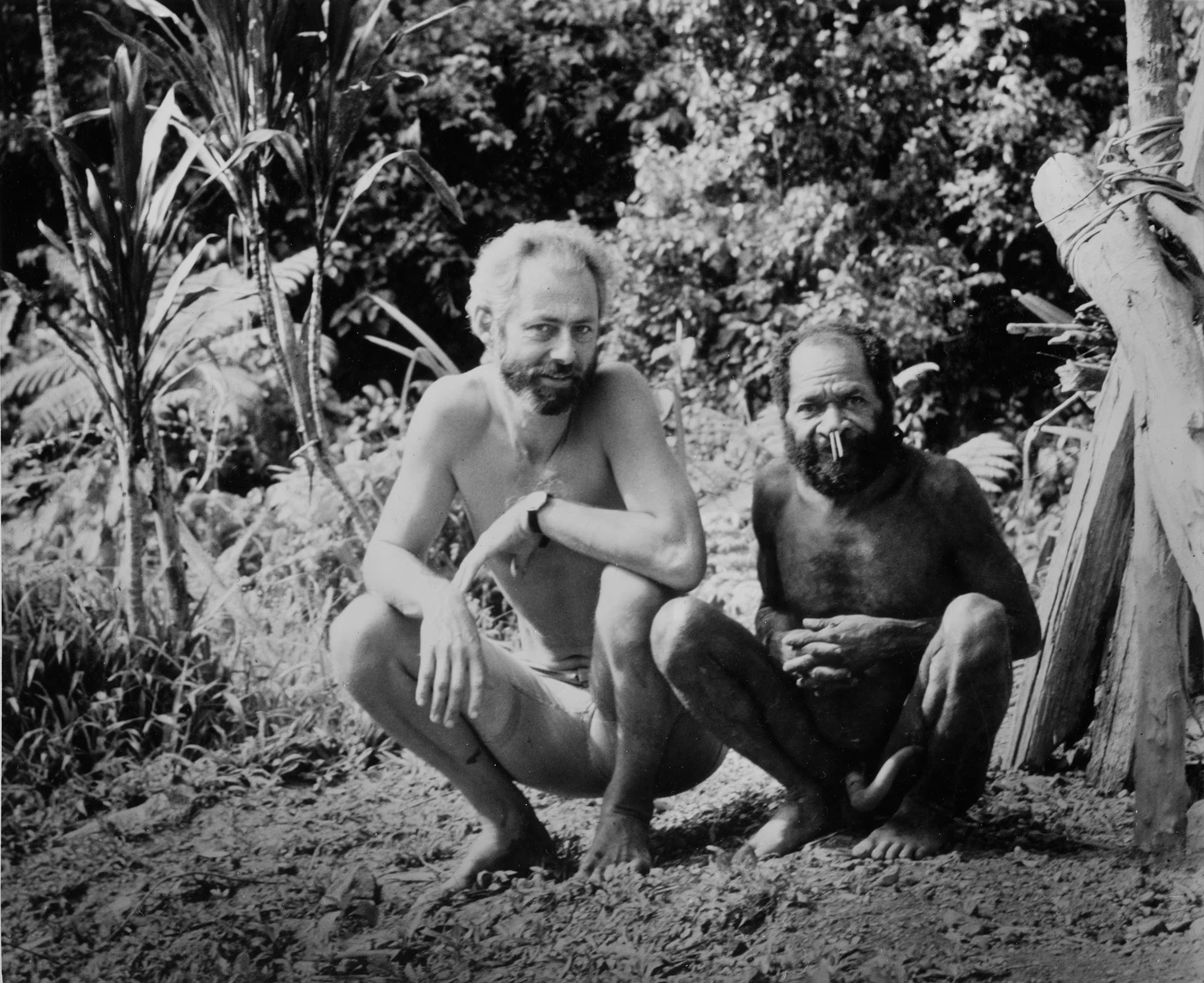
结构还是过程——如何理解交易主义 #
结构 #
既然我们强调对理论的理解应当置身于脉络之中,那么便无法绕开该理论回应、对话的对象。交易主义所对话的,正是此前在解释社会生活时强调「结构」概念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 [5]
[5] 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中,可以具体区分出以 Malinowski 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有时候它又被具体称作文化功能主义,以 Radcliffe-Brown 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两者都关注现实的社会结构,但具体的路径不同。法国的 Lévi-Strauss 创立的结构主义则完全不同于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其所指涉的结构是一种观念上、思维上的抽象的结构。
人类学对「结构」概念的强调还需要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 Émile Durkheim (埃米尔·涂尔干)。 Durkheim 强调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其实是「外在于个体的行为、思维或情感方式,它们被赋予某种强制力,并凭借这种强制力对个体施加控制」。社会事实是一种超然的存在,高于个体并且宰制着个体,因而宗教被 Durkheim 认为是一种集体的力,在社会群体中激荡起的力量,换句话说,社会决定宗教,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是基于高于自身的社会事实的信仰。甚至在《自杀论》中, Durkheim 试图在几乎最具个人色彩行为的自杀案例中找到背后更广泛的「结构性」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增加了一个人结束自己性命的可能性,譬如社会关系与道德纽带的瓦解」。
这种「结构」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乃至是 Lévi-Strauss 的结构主义。限于篇幅,我们不在此全面介绍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而以 Evans-Pritchard 在非洲的研究作为例子说明。
Evans-Pritchard 和 Fortes 合编的《非洲的政治制度》被视为政治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人类学的政治研究最早从「制度」层面开始探讨,试图回答「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而缺乏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非洲社会正是极佳的田野地点。Evans-Pritchard 一开始便直击问题核心:无国家社会如何维持社会秩序?问题的回答基于非洲社会以氏族、世系群作为支配性制度的特点,说明世系群和氏族如何通过发挥政治功能来维持社会秩序。他在后来的努尔人社会研究中提出的「裂变原则」是极为经典和精彩的例证:
从政治系统(世系群)上看,努尔人的部落由初级支系组成,初级支系又由次级支系组成,次级支系可再分出三级支系,而三级支系则由村落组成;从亲属关系系统(氏族)上看,努尔人的氏族可分为最大世系群、较大世系群、较小世系群和最小世系群。两套系统相嵌构成一种观念性的框架,每个村落可以围绕其最小的世系群来估算其与其他村落再谱系上的亲疏关系。假设现在有初级世系群 C ,分成次级世系群 A 和 B ,次级世系群 A 分为 A1 和 A2 两个三级世系群,次级世系群 B 分为 B1 和 B2 两个三级世系群, A1 和 A2 三级世系群又各自分出 A1-1 村落、 A1-2 村落和 A2-1 村落、 A2-2 村落, B1 和 B2 三级世系群也各自分出 B1-1 、 B1-2 和 B2-1 、 B2-2 四个村落。 A1-1 和 A1-2 村落的成员由于世仇而相互对抗,但当 A1-1 的村落成员与 A2-1 的成员爆发世仇,原本敌对的 A1-1 和 A1-2 会联合起来作为三级支系的 A1 一致对抗更为疏远的属于三级支系 A2 的 A2-1 ,当然,如果是 A1-1 与 B1-1 爆发世仇, A1-1 、 A1-2 、 A2-1 、 A2-2 也会联合一起作为次级支系 A 一致对抗关系上更远的次级支系B的成员。当敌意消除后,临时结盟的支系又会恢复先前的敌对状态——不同的裂变分支轮番联合对抗其他分支,又因内部的张力再次分裂,努尔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融合和分裂中维系社会秩序。
Barth 认为,在 Evans-Pritchard 这类结构功能主义中,政治组织是基于规则和规范的结构,乃至社会中个体的行为也是由他们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如亲属关系结构中的位置)来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Barth 眼中的结构功能主义或许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Barth 的交易主义则是着眼于行动者和他们的选择,以行动者作为导向,这是否带有「自下而上」的意味?如果按照这样的角度进行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归纳:结构功能主义是通过对作为某种抽象方案的「社会结构」进行描述来发现社会,而 Barth 的交易主义是描述个体行动如何「自下而上」地不断生成社会——是行动者的互动机制产生了某种广泛的社会模式。换而言之,社会不是结构功能主义者眼中的对象,而是行动中生成的过程。
过程 #
Barth 在《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中分析了巴基斯坦斯瓦特流域的政治组织,具体说明了政治组织是行动者参与的选择和策略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规则和规范的结构。
让我们援引部分内容了解背景,以更好理解 Barth 所想表达的意思。
斯瓦特巴坦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接近阿富汗地区,是个伊斯兰教社会。它是以整个居住地的山谷为区域体系的最大单位,其下分成十三个地区,再区分为村落、区、家。从政治制度来看,领导者是酋长,宗教上的领导者则是圣人。两个领域相互影响,而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不一定一致,彼此之间往往关系紧张,甚至存在着轮流替换的结构关系。(转引自《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p159-p160)
斯瓦特并未出现中央集权的现象,但没有类似于努尔社会的共同的继嗣群体,也没有基于扩展型亲属结构的政治系统,有的只是政治派系——酋长或穆斯林圣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土地稀缺的背景下,酋长和圣人主要通过将土地慷慨地分给无地者来提高他们的影响力,以得到足够高的声誉和多的追随者,进而成为政治领导人。其中,酋长主要通过氏族和世系群来继承土地 [6]
[6] 「氏族」不等同于「共同的继嗣群体」,「世系群」也不等同于「基于扩展型亲属结构的政治系统」。关于这几个概念,我一直不清晰,先留下 AI 的回答,见《概念 | 氏族、世系群、共同的继嗣群体和基于扩展型亲属结构的政治系统》——但仅此定然不够,还需要多方资料交叉验证。
Barth 强调酋长和圣人的政治关系中的自愿性质,追随者的规模大小反映着这些领导人相对地位与受欢迎程度,因此「慷慨」是斯瓦特社会的重要价值。为了赢得追随者,领导者将土地慷慨地分出去,类似于「夸富宴」 [7]
[7] 夸富宴(potlatch),北美洲原住民的一种赠礼仪式。在夸富宴上,东道主会赠送财物给参加者、甚至毁坏财物,以展现其财富及权威。
这样的视角源于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博弈论, Barth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互动的过程性模型。在该模型中,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体,而是身份——与特定社会地位相关的一系列权利与义务。人是各种身份的结合,身份参与互动,在互动中,各方努力确保获得的价值大于或等于他们失去的价值。同时, Barth 还借鉴 Goffman 的「印象管理」概念——印象管理同样是一个过程,人们在此间试图以符合个人预期目标的方式来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认为「根据一系列规则(印象管理的要求),可以从较简单的权利规定(身份)生成复杂而全面的行为模式(角色)」,据此观察更广泛的社会模式的出现。总的来说, Barth 认为对社会的理解应该基于行动者理性选择的特定互动机制所产生的某种广泛的社会模式。
黄应贵先生认为, Barth 一面延续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由社会整体来回答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另一面则以个人理性选择来挑战了结构功能主义在解释上过于静态和忽略个人地位的局限,还剔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将社会秩序问题限于正式的政治、法律制度上的偏见。不过 Barth 的交易主义取向也被认为假定所有人都在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这与市场经济模型的基本默认无异。
参考资料 #
- 马泰·坎迪亚:《剑桥大学人类学十五讲:人类学理论的流派与风格》,王晴锋译,金城出版社2024年版。
-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 维基百科编者. 散财宴[G/OL]. 维基百科, 2025(20250207)[2025-02-0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A3%E8%B4%A2%E5%AE%B4&oldid=86004999.